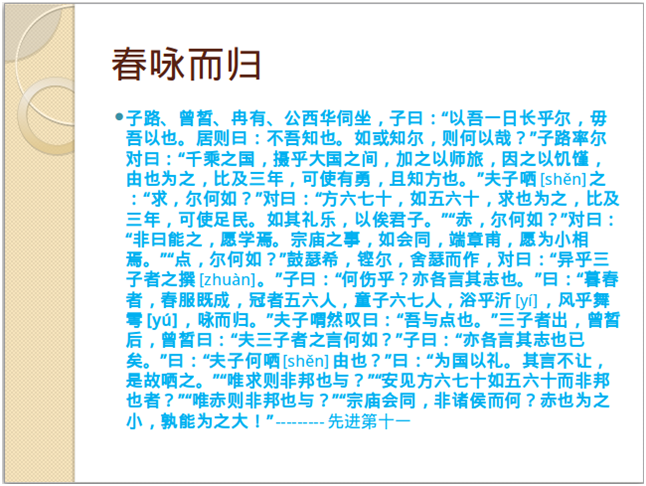说有子路,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有一天又坐在了孔夫子的旁边,子路特别忠实于孔子,他只要在孔子旁边,就一定和他呆在一起,他一天到晚就粘着孔子,所以呢,在上一篇里面也有孔子,在这里面又有它.孔子又说我们四五个人坐在一起又没事做了,孔子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比你们年纪大,就有所顾忌啊,不能这样.我们今天来讲一讲,你们平时都说这个世界没有知道你们的人,没有用你们的人,那如果有一天真的有人用你们啦,你们会怎么样?如或知尔,如果有人知道你,用你,则何以哉?你们会怎么样?子路这个人又非常的冲撞,马上就起来啦,率而对曰,子路是性格非常急躁的一个人,他的急躁孔子都有点担心,有一天孔子都说,子路这个人将来都不知道他怎么死,一语成谶,孔子这句话最终就应验了.确实不得好死,最后是被乱刀砍死的,当然在他死之前,也成就了一些成语,他说你们先别杀我,等我把帽子和衣服 整理整齐了再来,已经被围困在里面啦,没有办法了,所以他整衣冠而死.
子路这个人又急躁地说,千乘之国,摄乎大国之间,经过这些年年的战争啊,又因之以饥馑啊,又被饥饿所笼罩啊,国家财政也不行啊,由也为之,由是子路,让我去做吧,要不了三年,可使我们的士兵勇往无前,这个国家也治理得很好,人民也不感觉到饥饿,国泰民安,我的志向就是这样,结果话音刚落.夫子哂[shěn]之, 什么叫哂之?就是耻笑了一下,哼了一下,哼了一下以后就问另外一个人求,就说求而何如,冉有就是求啦,你的志向怎么样?冉有就说,方六七十,千乘之国我是治理不了啦,我治一个小的城邦,大约六七十里,或者还小一点,大约五六十里的城邦,让我去做,过三年之后啊,我可以让老百姓安居乐业,还能让他们知道礼乐,还能让他们尊敬君子.
孔子又说,公西华,你来说一说你的志向,公西华说他们讲得都太有能耐了,我愿意跟着他们学,但是我的能力不怎么样,我只愿意做一些宗庙里面的事情啊,如同祭祀啊,会盟啊,我希望我做一个主持人在这,端章甫,愿为小相,做一个主持人.
孔子又说,那增皙呢?你来说一说,增皙一个人在那弹着琴助兴啦,慢慢的琴声就没啦,于是就说,我这个人的志向和他们三个人都不同,不好意思说.孔子说没事,你说一说,反正我们聊天,也不与其它人知道,当然他是以为没有其它人知道,不知道被多少代人,一直到现在都知道啦.增皙毕竟是弟子,他推迟不掉了,就说,我的志向只想在春夏之交,暮春嘛,就是春天快要结束的时候,春夏之交去踏春啊,穿上春天里的服装,让微风吹过来,带着5-6个志同道合的朋友,带着我们的孩子,带着一群小网友,我们沐浴在春风当中啊,去唱歌跳舞啊,然后尽兴而归啊,这就是我的志向.这孔子一听,了不得啊,喟然叹曰,太了不起了,我的志向和你是一样的啊.等着冉有,子路和公西华走了以后啊,这个增皙还在后面,就问夫子啊,你说他们三个人的志向到底怎么样啊?他们三个人的志向到底好还是不好啊,你老是提倡君子之道,让我们去做官,让我们去发财,让我们去占领道德的制高点,让我们去引领社会的风尚,并且你认为天下风气不好就是君子不作为啦,那你这样说的话,这三个人应该是非常了不起啊.一个可以把千乘之国引导得非常好,一个可以把一个小地方引导得非常好,应该可以啦.
孔子说这不外乎说一说各自的志向而已呗,增皙看你在跟我打马虎眼啦,继续贴着问呗,所以学问学问,有时候弦外之音非常重要,这增皙听出你这话明明是在搪塞我啦,那夫子何哂[shěn]由也?那你为什么当时对子路要哂之?要耻笑一下啊?这就把孔子问上岸来了,没有办法,就说为国以礼,治理一个国家,最终的目的不是你把它治理得怎么样强大啦,而是让它以礼调和啦,也就是以仁爱为中心啦.里仁为美嘛,以仁为核心,建立在一个祥和的社会里面,这才是正常的国家,才真正治理好了,可是你看他说话的样子啊,言不由衷,这么急躁,这怎么能把一个国家带向礼仪呢?所以我来耻笑他.那难道冉有的话,说的治理这么小的地方也是这个原因?孔子说难道五六十里的不是一个城邦了吗?也是一个地方,不在大小,在于你的志向是不是在讲礼,两个人要不要讲礼啊?也要讲礼,和治理一个国家是一样的.
同样的话在<道德经>里面也讲过,治大国若烹小鲜,治理一个大国,和你在厨房里面调和小鲜,调和一个菜米油盐酱醋茶是一样的道理,事无大小,问题是你用什么样的思维去对待.因此冉有的志向也没有达到终极的目的.增皙听出门道来了,原来治理国家是以仁爱为中心,那公西华总可以了吧,他没有说治理国家,孔子就给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,宗庙会同,你每个国家,像我们国家每年也都是祭祀,什么祭奠皇帝的啊,祭奠泰山啊,天坛啊地坛啊这些都是祭祀,会同,会见外国的史宾,会盟嘛,召见外宾,像这些事情啊,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.这些并不比诸侯国家小,在这里面是传承礼仪,传承文明的地方,你说你会见一个外宾,没有礼仪的话,马上全世界都要知道啦.你说你祭奠一个泰山,连基本的礼仪都不知道,出现了差漏,曾经有个女子在孔庙面前,穿着很暴露的在那边拍照,像这些影响风俗的事情,在这一些地方,宗庙,祭祀的地方,重大的场合里面当一个主持人,比当一个诸侯要难得多,它引领风尚,引领一个国家的习俗,因此赤也为之小,孰能为之大!如果公西华这样的志向还叫小的话,那天底下没有比它大的啦.看出来了没有,孔子在治理国家上,治理人缘上,孔子强调了礼,强调仁,强调了名利.但在个人的志向上,他让他摆脱名利的纠缠,你没事几个人在一起聊聊天多好,几个人一起去修行多好.为什么要在名利里面打转呢?因此儒家的最高经典一定是非儒的.我帮助你一定是希望你不再需要别人的帮助,你能自强自立,我的帮助是有效的,我帮助了你,最终你依靠了我,我的帮助是无效的.除了夫子自己的志向以外,他的两个志向很简单是不?他对弟子的赞扬里面也特别重视颜回.
他对颜回讲的一句话那是非常有名的,那是《雍也第六》里面讲的,子曰:“贤哉回也!孔子说,颜回简直就是圣贤啊,一箪食,一瓢饮,在陋巷,人不堪其忧,回也不改其乐。贤哉回也!”一顿粮食,一瓢水,在一个很简陋的地方,别人都感觉无法生活下去了,但是颜回还是非常地快乐.所以他说颜回非常地贤能.
我们讲了这么多,只是告诉大家,<论语>不是儒家的最高经典,儒家的最高经典或者所有宗教的最高经典,一定是不可言说的那个根本.
既然不是,那孔子他要做什么呢?孔子带着他的三千门徒,七十二贤人,他们要做什么?他们要做一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,要去制一个大的净化器,把这个世界给净化下来,这个能成功吗?不会成功,我们也知道不能成功,孔子也知道不能成功,但是总得有人去做,在《论语?宪问》这一章里面,就说了这样一个故事:子路宿于石门。晨门曰:“奚自?”子路曰:“自孔氏。”曰:“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?” 有一次子路在石门那个地方住下来了,早上过城门,守门的门卫就问他,你从哪里来,子路就说我是从孔夫子那来的,守门的那个人就说,就是那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吗?连守门的人都知道孔夫子做的事情非常伟大,你们听了我前面讲了那么多序论,一定也能理解孔子的良苦用心,行,你培养一个君子吧,这个君子还得有所作为,还得去争名夺利,你说他去争名夺利吧,他又不是为了名利的目标,他是为了占领道德的制高点,去引领这个社会的风气.多么伟大.最后君子也所了,君子很少的,君子这样少,怎么可能占领 所有的制高点呢?不可能,但是不可能就不做这样的事情吗?一定要做的.